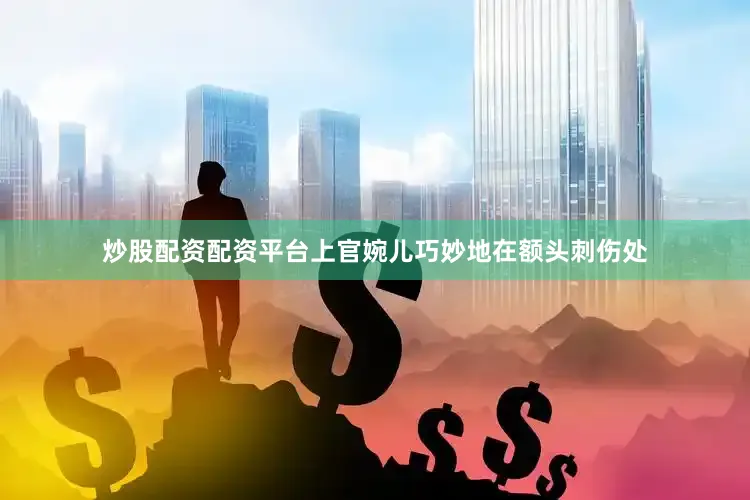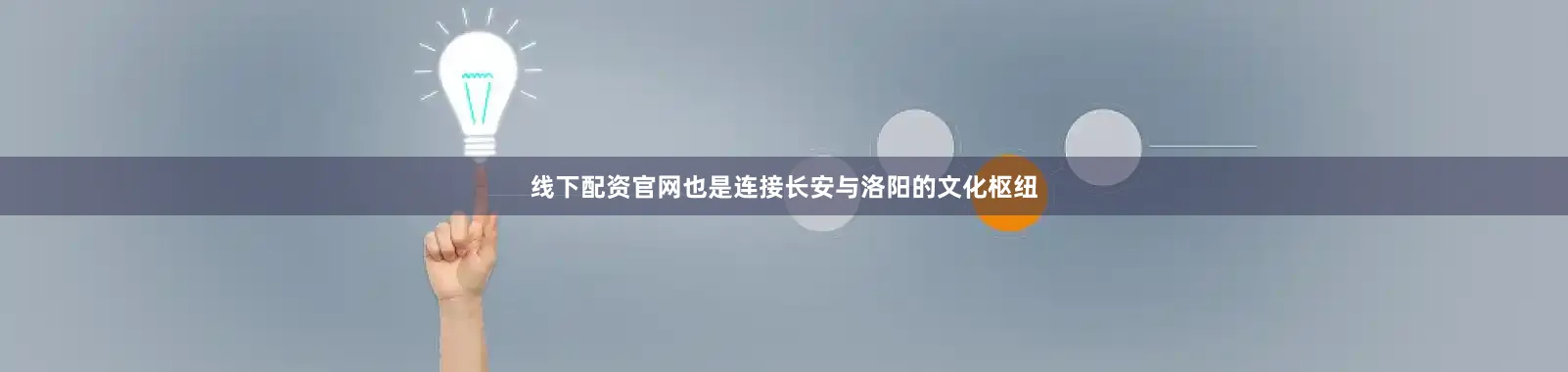
送卢处士归嵩山别业
刘禹锡
世业嵩山隐,云深无四邻。药炉烧姹女,酒瓮贮贤人。
晚日华阴雾,秋风函谷尘。送君从此去,铃阁少谈宾。
赠苏少府
白居易
籍甚二十年,今日方款颜。相送嵩洛下,论心杯酒间。
河亚懒出入,府寮多闭关。苍发彼此老,白日寻常闲。
朝从携手出,暮思联骑还。何当挈一榼,同宿龙门山。
一、刘禹锡《送卢处士归嵩山别业》:隐逸绝尘的清幽之境
刘禹锡的诗以 “送别隐士归山” 为核心,通篇围绕 “嵩山隐居” 展开,意境清冷、超脱,充满对尘世隔绝的向往。
首联破题:“世业嵩山隐,云深无四邻” 直接点出嵩山是卢处士的 “世业” 隐居之地,“云深无四邻” 以 “云深”“无四邻” 勾勒出嵩山的幽深、静谧,仿佛与尘世隔绝,奠定 “清幽绝尘” 的基调。 生活细节见心境:“药炉烧姹女,酒瓮贮贤人” 中,“姹女”(道家指丹药)与 “贤人”(代指酒)是隐士生活的典型符号 —— 炼丹养性、饮酒自适,无官场纷扰,无世俗应酬,尽显超然物外的闲适与洒脱。 送别环境的烘托:“晚日华阴雾,秋风函谷尘” 以嵩山周边的地理意象(华阴的雾、函谷关的尘)渲染送别时的氛围:晚日西斜,雾起风凉,尘世的 “尘” 与嵩山的 “云” 形成隐性对比,暗喻卢处士即将脱离 “风尘” 回归 “云深”。 收尾的对比强化:“送君从此去,铃阁少谈宾” 中,“铃阁”(官署)的 “谈宾” 与嵩山的 “无四邻” 形成鲜明对照,凸显隐士归山后 “隔绝尘嚣” 的清净,进一步强化了 “隐逸超脱” 的意境。 展开剩余75%2. 白居易《赠苏少府》:闲居挚友的温情之境
白居易的诗以 “赠别官员友人” 为核心,聚焦于嵩洛一带的友情与闲居生活,意境温暖、平实,充满对日常情谊与清闲时光的珍视。
送别场景的日常感:“相送嵩洛下,论心杯酒间” 点明送别地点在 “嵩洛下”(嵩山与洛水之间),“论心杯酒” 无离别之悲,反显挚友间的坦诚与闲适,开篇即奠定 “平和温情” 的基调。 人物状态的共鸣:“苍发彼此老,白日寻常闲” 勾勒出两人年老后的状态 —— 鬓发已苍,日常清闲,不刻意追求官场浮华,而是珍惜 “寻常闲” 的时光,体现对平淡生活的满足。 相处细节的暖意:“朝从携手出,暮思联骑还” 以 “携手”“联骑” 的日常互动,写尽挚友间的默契与温情;“何当挈一榼,同宿龙门山” 则以对未来同游龙门山(嵩山附近)的期盼,将友情延伸至对自然闲游的向往,无隐逸的隔绝感,反显 “尘世中的清闲”。 官场与闲居的平衡:“河亚懒出入,府寮多闭关” 暗写苏少府不热衷官场应酬,与白居易自身的 “闲” 形成共鸣,诗中无对官场的批判,而是在官场框架内追求 “闲” 与 “情”,意境更贴近 “世俗中的安宁”。二、与嵩山的地理位置关系:核心隐所 vs 周边背景
嵩山位于今河南登封,是中原腹地的名山,周边有洛水(洛阳)、龙门山(洛阳南)、函谷关(今河南灵宝)、华阴(今陕西华阴,近潼关)等地理标志,在唐代既是自然名山,也是连接长安与洛阳的文化枢纽。两首诗对嵩山的地理依托各有侧重:
1. 刘禹锡诗:嵩山是核心 “隐逸空间”,周边为 “尘世参照”
嵩山的核心地位:“世业嵩山隐,云深无四邻” 直接将嵩山定义为卢处士的 “世居隐所”,是隐士的精神家园与物理归宿,地理上是隔绝尘世的 “原点”。 周边地理的对比功能:“晚日华阴雾,秋风函谷尘” 中的华阴、函谷关,是古代长安至中原的交通要道(函谷关为 “关中咽喉”,华阴是西入关中的门户),象征 “尘世奔波”;而嵩山 “云深无四邻”,与 “华阴雾”“函谷尘” 形成地理空间上的对立,强化 “隐” 与 “俗” 的分野。2. 白居易诗:嵩山是 “周边背景”,嵩洛为 “友情场域”
嵩山的背景属性:“相送嵩洛下” 中的 “嵩洛” 指嵩山与洛水之间的区域(今河南洛阳周边),嵩山并非核心目的地,而是送别与友情互动的 “地理背景”,象征中原腹地的文化与自然交融的空间。 周边地理的亲和性:“同宿龙门山” 中的龙门山(洛阳南,伊河两岸,距嵩山约百公里)是嵩山文化圈的延伸,与嵩山共同构成 “闲游空间”,而非隔绝之地。诗中地理(嵩洛、龙门)是官宦阶层日常活动、交流的场域,体现嵩山周边 “尘世中的自然依托”。三、地缘关系:隐逸符号 vs 官宦闲居依托
唐代的嵩山不仅是自然山景,更是承载文化意涵的 “地缘符号”:它地处中原核心,北接洛阳(东都),南连颍川,既是隐士避世的理想之地,也是官宦阶层休闲、交流的近邻空间。两首诗通过地缘关系的不同呈现,折射出唐代文人对 “出世” 与 “入世” 的不同选择。
1. 刘禹锡诗:嵩山作为 “隐逸地缘符号”,对立于官场
地缘意涵:嵩山的 “云深无四邻” 与 “铃阁(官署)” 形成地缘上的 “隐 — 俗” 对立,代表与官场、尘嚣彻底割裂的 “隐逸空间”。卢处士的 “世业嵩山隐”,将嵩山转化为家族传承的隐逸符号,体现唐代文人对 “不仕而终” 的价值认同。 文化逻辑:依托嵩山远离政治中心(长安、洛阳)的 “相对隔绝性”(虽近洛阳,但 “云深” 营造心理距离),强化 “隐士文化” 的地缘根基 —— 名山为隐,既是自然选择,也是文化传统(如东汉以来嵩山即为隐士聚集之地)。2. 白居易诗:嵩山周边作为 “官宦闲居地缘依托”,连接尘世与自然
地缘意涵:嵩洛一带(嵩山与洛阳之间)是唐代东都文化圈的核心,既是官场活动的区域(苏少府为 “少府”,属地方官),又因靠近嵩山、龙门等自然景观,成为官宦阶层 “忙里偷闲” 的空间。诗中 “携手出”“联骑还”“同宿龙门”,体现嵩山周边 “近官而不扰,近自然而不隔” 的地缘优势。 文化逻辑:依托嵩山与洛阳的 “近距离地缘关系”(嵩山距洛阳约百公里),官宦无需彻底归隐,即可享受自然与友情,体现唐代中晚期文人 “吏隐” 思想 —— 在官场中求闲,以名山周边为 “缓冲带”,平衡入世与自然需求。总结,刘禹锡的诗以嵩山为核心隐逸符号,意境清幽绝尘,地缘上强调 “隐与俗” 的对立;白居易的诗以嵩山周边为友情与闲居背景,意境温暖闲适,地缘上体现 “官与闲” 的平衡。两者通过对嵩山及其周边地理的不同书写,展现了唐代文人对 “出世” 与 “入世” 的多元选择 —— 或追求彻底的隐逸超脱,或珍惜尘世中的闲情与友情,而嵩山这一地缘符号,恰承载了这种文化多样性。
发布于:河南省垒富优配-配资官网-配资炒股合同-深圳十大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